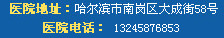印光法师,俗姓赵,名丹桂,字绍伊,号子任,法名圣量,字印光,陕西郃阳(今合阳)孟庄乡赤城东村人,自称常惭愧僧,又因仰慕佛教净土宗开山祖师——当年在庐山修行的慧远大师,故又号继庐行者。
大师生于清咸丰十一年(年)腊月,少治儒学,喜读程,朱之书。清光绪七年(),大师二十一岁,出世缘熟,遂于终南山南五台莲花洞寺出家,礼道纯和尚为师。
翌年于陕西兴安双溪寺,依印海定律师座下受具足戒。二十六岁,赴净土道场红螺山资福寺念佛,自号继庐行者以明其志。次年正月朝礼五台,仍归资福。其间除念佛外,深入研习大乘经典,妙契佛心,径路修行,理事无碍。
三十岁时,至北京龙泉寺为行堂,三十一岁至圆广寺,继续专修念佛法门。光绪十九年至普陀山法雨寺。
大师在佛教徒中威望极高,与近代高僧虚云、太虚、谛闲等大师是均为好友;弘一大师更是拜其为师,其在当代净土宗信众中的地位至今无人能及。最被人称道的是,无论是谁,只要写信请教,大师都回信指点迷津,由其回信集结而成的《印光大师文钞》,被认为是佛教徒尤其是净土宗信众的修行宝典。
法师是由儒而入佛的;他别号“常惭愧僧”,以此可以窥见他向佛后一生所为。他是从佛道而出,受惭愧心所驱的。一般人陷于重重的罪恶中,善根力非常薄弱;唯有惭愧的重善轻恶,能使人战胜罪恶,使善根显发而日趋于增进。印光法师一生无论为法为人,始终循着这种倾向光明的正觉。身体力行,潜修佛道,直指本心。做事但求无愧我心,本着对自己负责的态度。这样做的客观后果,却使众生受惠,独善其身收到了兼善天下的效果。倘若世间为人,皆照此行事,对自己的言行负责,即人间早已成为充满喜乐清净的福地,人皆可以成佛了。
印光法师一生随遇而安,身教胜于言教,淡泊清苦,他把自己数十年来参研佛法的心得体悟都融于日常的一言一行中。他是北方人,喜欢吃馒头,每次吃饭只有一碗粗菜,吃完以后用馒头把菜碗擦净吃光,或者用开水汤洗饭碗。他住在上海太平寺时,有居士请他吃斋,他不去,再三请,他才嘱咐只上一盒馒头,一碗豆腐渣,居士答应照办,他才赴斋。他住的房间都是自己打扫,穿的衣服也都是自己洗,一直到79岁高龄还坚持这样做。
有一次他在上海的太平寺,有一居士去拜访他,却见他在院子中自己洗衣服。在苏州报国寺时,真达和尚请他到灵岩山,已经替他备好了轿子,他却从上山到下山,始终拄杖步行,坚决不肯坐轿。法师一生都是如此,无论在何种情况下,都不摆一点架子。他自己就曾对人说过:“我不摆架子,也就不怕倒架子。”可见法师为人,有着很强的独立精神,决不肯徒受别人的恩惠,亦不肯以自己的存在成为别人的负担,超然于物外。
“九?一八”事变爆发后,法师以76岁高龄每日讲法两小时,号召全国佛教徒为抗日救国作出贡献。当听说抗战中绥远的灾情严重时,把当时所收余人皈依求戒的香仪多元都全部捐出,并附上自己原存的多元,长安经过兵灾以后,人民的生活非常艰苦,法师就将印行《文钞》的款项元,托国人速速汇往赈济。年,陕西省大旱,法师听到消息后,马上取出存折,令人速汇元。汇完以后,令人查帐,发现折中所存仅百元,而报国寺的一切需用,都靠这点钱了,法师对此也不介意。法师把自己的这些行为与保护佛法连在一起,把救助人的实际苦难视为到普渡众生。法师曾说:“救灾即是普渡众生,亦是保护佛法。”其言词中爱国爱民之情,是何等的恳切。
法师对于佛法的理解,绝不脱离世间而虚妄谈佛。他启示弟子的是从“人乘”直达佛乘的一条学佛路线。在他的《文钞》中有这样几句话:“敦伦尽分,闲邪存诫,诸恶莫诈,众善奉行,真为生死,发菩提心,以深信愿,持佛名号。”即是从人伦出发,在处理好上下左右关系的同时,尽自己的本分,把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工作或责任做好。法师的话是极平易朴实而又见根本的。
弘一法师很仰慕印光法师,曾多次求拜,然而印光法师为人低调,不愿收徒,最终被弘一法师用香火烧自己的臂肉,以“臂香”拜师而感动,这才得到印光法师的同意,收为弟子,共结法缘。随后,印光法师请弘一来到他身边住了半个月,言传身教。法师虽然精通种种佛法,而自行劝人,则专依念佛法门。他的在家弟子,有许多是受过高等教育和在欧美留过学的。可是对于佛法之哲理,法师绝不和他们一起高谈阔论,只是一一劝其专心念佛,这种作风对弘一法师也有很大的影响。
印光法师为人坦诚,不图谋虚名,且风骨嶙峋,他80岁生日时,道友准备为他筹办80寿辰祝寿活动,然而法师却坚决反对,弟子只得作罢。
年,印光法师在大众念佛声中,如入禅定,笑容宛然,安祥逝矣,世寿八十。
印光法师的一生,诚如弘一法师的评价:“弘扬净土,密护诸宗,明昌佛法,潜挽世风。所摄皆具慈悲,语默无非教化。三百年来,一人而已!”
转载请注明地址:http://www.abmjc.com/zcmbwh/6374.html